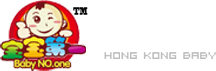2023年10月20日到26日的白天,在乌镇西栅的蚌湾剧场门口,永远排着等待看戏的队伍,最长时可绵延至河边。9月,乌镇戏剧节青年竞演比赛(以下简称“青赛”)线上预约的免费票在开票伊始便被抢空。这是每年乌镇戏剧节最重要的单元之一,也是唯一的竞赛单元,18组青年戏剧人的作品中,将会决出小镇奖最佳戏剧奖、最佳个人表现奖、特别关注奖。
蚌湾剧场外的围栏前立着一块指示牌,显示本场青年赛能进ⅩⅩⅩ位观众。剧场内,18组青年戏剧人的作品轮流上演;剧场外的一面石墙上临时挂了屏幕,供无法入场的观众观看直播,烈日下,总有五六排热心观众席地而坐。
.jpg)
2013年至今,乌镇戏剧节办了10年,青赛也比了10年。蚌湾剧场得名于此处最早的地名,黄磊觉得不错,“蚌湾里面有好多的蚌,每一个蚌里都可能藏着一颗奇妙的珍珠。”
乌镇戏剧节发起人之一、在北京电影学院任教多年的演员黄磊对传统艺术教育抱有“深刻的感激”和“深刻的关于不足的反思”,一些在学校无法实践的构想,他带到了乌镇戏剧节。今年,第十届乌镇戏剧节开幕前两天,在致青赛的手写信中,黄磊写道,“最初的最初,乌镇戏剧节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念头时,青年就已经是这个节的主人公,一切的缘起与目标皆是为了青年们。”
青赛面向有志于从事戏剧行业的青年,规则很简单:乌镇戏剧节3位发起人一人提一个道具,组成该年度命题——利用这3个道具,在20-30分钟内,不超过5个人,排演一出原创戏。
今年5月,乌镇戏剧节发起人黄磊、赖声川、孟京辉为青赛出题:世界名画,火车票开云全站官网平台,马。“3个道具的根本目的并不是考验你道具如何使用,是考验你怎么利用环境,找有效的舞台支点,把单位时间内戏的能量密度发挥到极限。”青赛评委李博说。8月,超过500份作品交上来;9月,18组入围作品公布;10月中旬,在乌镇戏剧节展演的分组抽签名单出炉。
青赛的小舞台这些年来已经走出了不少戏剧人。2013年,陈明昊执导的《巴巴妈妈》夺魁,今年他凭借在《漫长的季节》中的表演被大众熟知;2015年,吴彼以《静止》获得最佳戏剧奖,今年他既是青赛的评委,也是赖声川新剧《长巷》的演员。吴彼曾说,乌镇是他事业最大的转折点,“你们可以没有成本,什么都没有,但尽情去做你们想做的事,而且给大家一个舞台,这么多人来看。”
李博以选手身份参加了前三届青赛,作品都进入三甲;第四届起,他成为青赛评委之一,负责从几百个作品中选出18组入围作品;再从18组中选出6组决赛作品。
20岁出头时,李博在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念书,在象牙塔里享受自由和浪漫;后成为大学老师,“一直觉得没有目标和出口,因而非常迷茫。”参加乌镇戏剧节对他来说有方向性的意义,他说,这是一个能让更多人了解他戏剧理念的途径。
在乌镇的10天里,我在蚌湾剧场度过了相当久的时间,从这些青年剧作中,能看到对男女情爱消逝的展现,母女、父子间的牵绊带来的隐痛,个体对世界撕裂的思考。
获得最佳戏剧奖的《五楼九楼》故事设定在一架故障电梯中,五楼的男生和九楼的女生在半个小时里,反思了自己的亲密关系,一个觉得自己困住了男友,一个可能被女友困住。他们都想要逃走,拿假想的火车票去北方看极光。
获得特别关注奖、最佳个人表现奖的《蚌与珍珠》,主角是控制欲极强的母亲,在心理医生的帮助下,揭开了自己少女时期受侵害的创伤。结尾,女儿给母亲拍照,母亲回眸,变成一幅《戴珍珠耳环的少女》。
同样获得特别关注奖的《我和刘红梅在车站》从头至尾只有一个演员,“我”离开了大城市回到家乡成为游乐园旋转木马项目的工作人员,几次遇见“她”(在家乡过了一辈子的姥姥),15岁的她要偷偷下河游泳;二十多岁的她想去北京上海,火车票丢了急得直哭;82岁的她单薄、沉默、老态,时间在她身上加速流转;最后,“我”带着6岁的“她”摸遍了旋转木马。
戏剧节期间有一晚,李博在枕水雕花厅排队进场看孟京辉的新戏,听一位观众吐槽某部青赛的戏。李博觉得挺有意思,这恰恰体现了青赛标准的多元化,“确实那个戏观众褒贬不一,但是10年来青赛舞台上它是唯一以这种方式演的独角戏。我们要鼓励,没准将来会形成独特的风格。年轻人的戏就该做很多探索,如果把戏做得都非常工整,就是赖老师了,对吧?”
本届青赛决赛入围作品 《打开打不开的窗》 剧组谢幕(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张宇欣/图)
在决赛名单出炉后和戏剧节结束后,李博两次接受了《南方人物周刊》采访。以下是李博的口述:
10月26日我们商量6个入围剧目,要拍一个评委商量决赛名单的官方照,我们都正襟端坐,拿着评戏的单子。后来是谁说到了一个观点,程耳导演第一个站起来了,说,不行,这舞台这么难得,这个戏一定要是戏剧的语言才行。后来全都站起来了,争执:什么是对舞台的敬畏、什么是话剧的语言、小剧场到底该怎么演、对3个道具到底该怎么用、表演超时了该怎么办……
青赛是一个学校,允许你有可爱的瑕疵。不过当时以瑕疵为优点入围的戏,到了青赛舞台上几乎都走样了。
有个戏,8月20号报名截止,我看他们8月19号录的,再不录来不及了。录像在一琴行,第一个镜头还在晃。他们演的是轻喜剧,演员要绝对松弛,恰恰他们可能就是照着不入围来演的,现场碰出了很多有灵性的、高级的喜剧台词,耳导他们组就把这戏给提上来了。我正在外地开会,真是无聊,就戴耳机一边看录像。他们呈现得既松弛又好玩,我看得特别高兴。演员忘词了嘎嘎乐,我也嘎嘎乐。
后来宣布入围,组委会打电话,签确认函,设计海报,到乌镇,安排三次公众排练,接受一次采访,再有几次排练,接着三轮演出。他们开始认知到原来这是个比赛,紧张了。一紧张人就变得不自由。
官方微博把决赛名单公布出去,有一条留言说,这6个戏个个扎实,恭喜他们。这个评价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鼓励,有的戏可能看上去很好很丰富,但是很飘,一咂摸没味道;有的看上去四平八稳,但是整个呈现有年轻人很难得的稳重。
今年是我做了7年评委、见到作品整体水平最高的。今年决赛6个是线个,我们最后是在取舍。恰巧碰到我很喜欢的戏,有的评委特别不喜欢,我们两个就一直争辩,但这是学术上的,不涉及个人。在单位工作,我往往会回答“是”“对,您说得对”,但在乌镇戏剧节不存在这个问题,我跟赖老师也争过。
今年道具是一匹马、世界名画、火车票。除了表演、文本以外,最重要的还是看3个元素怎么用,因为这个比赛是由3个元素撑起来的。我们在评判时,如果两个戏呈现都差不多,我们就看道具了。3位老师每个人给一个道具,就是为了防止把旧作拿来改编。
对道具的使用,特别考验一个剧组的专业程度。比如咱俩打架没打出胜负来,突然出现一把刀,谁都想去抓刀,这个刀引起了戏剧的转折,改变了戏剧的走向,这是比较普遍的用法。
对道具,只提一下,这是最简单的;还是它对戏的转折起关键作用?还是它作为一个意象、象征,贯穿整个戏,始终在你脑海当中徘徊?这是完全不同的三个层级。
今年道具里难的是世界名画,因为我们中国人很少有看画展的经历。有的戏是戏仿《戴珍珠耳环的少女》,有的是家人把她的作品当成世界名画,有的是演员去模仿《呐喊》,都挺可爱。
《我和刘红梅在车站》,我们几个评委全体通过进决赛。我想它进决赛和道具的使用应该有分不开的关系。马的意象是贯穿通篇的。我们学表演,道具作为舞台支点也好,推动剧情发展的关键物品也好,怎么也要在舞台上出现一下,但这个戏里没有出现。剧本提到旋转木马的游戏,“我”在舞台上一圈一圈走,像旋转木马一样,碰到“我”的姥姥,每走一圈“我”看到不同阶段的刘红梅,都发生了不同的事情,关乎着刘红梅的命运。最后“我”又回到了工作岗位,给其他小朋友来开旋转小木马。这么清新,这么自然。
那天我在朗读会上还说,微博140个字就能获得鸡汤,快手抖音一分钟能够达成你所有的欲望,为什么有人会在剧场里消耗两个小时的生命,去看戏?首先这个戏一定是有温度的。第二,你戏里聊的东西,是抖音快手微博不常看的,要带领观众去关注到生活里面我们不曾关注的人。
到现在为止,在历届青赛里选出一部戏,我觉得最好的是2016年的《嘎玛》(记者注:当年的青赛题目是一滴血,一个旅行箱,一颗流星。《嘎玛》主角是一对母女,多年来,阿妈放不下离家修行、成为活佛的阿爸,活佛已死,阿妈坚信活佛可以在49天内转世回到家中,寄希望于女儿嘎玛怀孕;嘎玛怀的孩子却是格桑花转世,孩子也夭折了。母女二人打算各自去朝圣,在去神湖的路上最终和解),上海戏剧学院两个研究生做的,是青赛历史上唯一一次最佳个人表现奖和大奖全给了一个团队。在舞台上演信仰,一般都往复杂里演,但那个戏讲得特别简单,一把椅子,两个女孩,其中一个女孩演了两个角色(念念不忘丈夫的阿妈,和格桑花转世的孙女),就那么简单,却讲得那么通透。她们磕完长头之后往远处一看,一个冷光打过来,哗,那是一片湖。响起藏族的音乐,感觉我们就在雪域高原里。
从第一届到现在,所有得大奖的戏,都是以小见大,踏踏实实讲生活。你从西栅随便抓一个人,10岁以上90以下,坐那儿都能看懂。
青赛的舞台离观众很近,真,是最重要的。你的戏剧内核是通过一个小事儿,还是假模假式地通过一个哲学事件告诉我们?我特别不喜欢拿腔拿调、煞有介事地非要告诉我们点什么,或者强行灌输什么。包括评委投票,这种戏结果都不好。年轻人的戏剧不用做那么复杂,上来探讨To be or not to be,对不起,您真没那功力,有时候想的跟演出来的是两回事儿。我还是希望能把故事讲清楚:有起承转合、人物性格、矛盾冲突、主题立意,哪怕没有立意,都很难得了。
你看刘添祺的《鸡兔同笼》(记者注:青赛最佳戏剧奖获奖作品)多简单,儿子去监狱里边看他爸,两个人有一段谈话。小戏里有大世界。
我还是觉得年轻人不用玩酷、玩炫,踏踏实实的,把精力放在故事上,故事怎么架构、怎么展开;表演一定要收敛。我特别讨厌短视频里能刷到的那种撒泼表演,但是很多人可能受了影响,觉得我们的戏一定要“起”。我跟青赛的选手讲,内心波涛汹涌、外表平静如水的戏最难演。马龙·白兰度、罗伯特·德尼罗、阿尔·帕西诺碰到让他信仰崩塌的事儿,有一个在嚎叫吗?他的情感是蓄水池,要出来多少就出来多少。
在舞台上我们也需要学习这个。表演呈现一定要含蓄、克制、隐忍,千万不要因为观众的呐喊、叫好而把这个戏演飞了,从而喧宾夺主。有的戏呼声特别高,但我们就觉得有点讨好观众,演了一次,知道哪个包袱在哪个地方,第二次就拼了命演,甚至都没有控制、没有节奏了。《我和刘红梅在车站》就特别稳,不迎合观众。
我们看报名录像,有大量独角戏。很多像是我们上学那时候做的——一个人在单位时间里面遇到了一个困境,通过人和人、和自然环境的斗争,把问题推向一定的高潮。但我们应该给来乌镇的观众看新东西、线个独角戏,像《我和刘红梅在车站》,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独角戏表演了,更多的时候是在说话、在流露,在特别平淡的状态里,但内心是有内容的。
我觉得乌镇的蚌湾剧场、青赛就是中国年轻戏剧人的一块实验田,你只要有能力,可以把你自己实验的东西放在舞台上,观众是宽容的,我们评委也是宽容的。
蚌湾剧场外,所有本届青赛作品的海报贴在灰石砖墙上(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张宇欣/图)
我33、34、35岁那三年作为选手参加青赛,是很难忘的,也很值得。第一年我做了12个剧目里面唯一的喜剧;第二年我做了唯一的肢体剧,没有台词;第三年我做了唯一的蒙太奇戏剧,靠光来解释表演。现在我依然当老师,但肯定排不出那三年那样的东西了,人的经历越来越丰富,胆子越来越小。尤其在大学里工作,想象力就没有那么天马行空。
投青赛第一年,我们在学校每天晚上排到两三点,排着排着学生要放弃,说这么些评委,规格肯定高,入围不了。我说,当老师这么多年我也做科研、也投奖,不收报名费的比赛肯定是好比赛。
我教书是在公办的二本院校,学生从招生上和北电中戏的就有差距了。我第一届一块儿比赛的学生,“成活率”是很高的,有一个在开心麻花,一个在大连市话剧团,一个现在是带货主播,做得也非常好,我看过他的直播,他的直播技巧和表演是挂钩的,他会现挂、砸挂,与其说在看他直播,倒不如说在看他演一场戏。
我在大学也排戏,也排乌镇的戏,一个脑子有时候得分成两种思路。中国的大学其实都一样,大学的教育有大学的特点。所以年轻人拿到乌镇戏剧节的道具,可能很兴奋,因为终于有机会能做一个真正喜欢、有生活质感的喜剧、悲剧或者荒诞剧。咱说句特别不好听的话,乌镇的戏也不是说你在乌镇演了以后就能天天演,就这么10天,拿了大奖,(持续)上演的机会也很小。有的戏很稚嫩,但是因为它的场面足够宏大,一直在演。
我还是鼓励年轻人都应该去戏剧节看戏、比赛。全国的戏剧爱好者凑到一个地方,一起聊聊戏,这种珍贵是你在脑海里边一辈子都挥之不去的。
乌镇戏剧节的目标非常明确,抓住5%的人,这戏剧节就能办。我们是没有办法像一些电影节那样,有一个链条式的、推波助澜的辅助,给钱拍,上映、上线。戏剧还是小众,全国的银幕数量肯定比剧场的数量多得多。但我们就是为了深深地给他们打上一针强心剂。每一年乌镇青赛的观众里都有往年入围的选手,今年没投、投了没中的,回乌镇看戏。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选择,如果不做戏剧,我们当然能理解,因为能够活着就不错。如果要做戏剧,那就做出一个好的来。